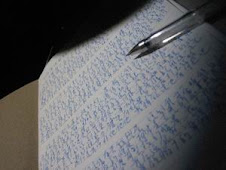6號、偉、正、泥鯭:
發生如此大事,希望你們心情還好。
那夜,瞥見你們的身影在「香港巨蛋音樂節」海報出現,我下巴着地,內心絞痛。及後整天,網上亂箭齊飛,罵聲滔天,我跟許多支持你們的人一樣,心情浮躁,坐立難安,食慾不振。這種感覺,應該叫「肉緊」。
肉緊,只因我們喜愛RubberBand。半年前,你們首次在紅館開騷,我在場。開場之前,同行友人嘀咕:「我啲同事而家喺機場,睇BIGBANG。我唔敢提自己喺紅館,睇RubberBand……」的確,你們踏上紅館台板的年頭,韓流大行其道,反之香港文化,光環褪色,裹足不前,許多人不屑一顧。然而散場時候,我發現友人微笑點頭,也聽見身後年輕觀眾激動地說:「好感動!」作為新一代流行標誌,你們能夠打動人心,全因「肉緊」。
為香港肉緊
我讀過雜誌,知道你們的成長背景,跟萬千「香港仔」同出一轍:泥鯭與阿偉在屋邨長大,試過被(自稱)黑社會的人欺凌; 6號八歲由澳門移居深水埗,與南亞社群和草根百姓一同成長……出道之後,你們記掛屋邨,心繫舊區,於是少唱國語,堅持為這城的快樂與哀怨發聲高歌,只因你們跟廣大「香港仔」一樣,為香港肉緊。
香港流行文化,之所以曾經風靡一時,全因它立足平民,跟街坊一同抱怨加價熱潮、賣身契約,訴說莫大毛、六嬸和三太公的日常瑣事。你們的音樂,同樣與百姓同呼同吸——豬肉檔、板間房、影視店、鐳射舖在歌詞出現;非洲移民、夜歸族、接線生的故事被仔細勾勒,大肆宣講……你們愛講小故事,肉緊平民心跳。
「在高牆與雞蛋之間,我永遠站在蛋的一方。」村上春樹這句名言,近年時常被媒體引用。我眼中的RubberBand,跟村上一樣,為雞蛋肉緊。你們會慨嘆「這小店快要撐不了」,會控訴「八百個超市吞噬着城市」,會堅持「夏季那夜燭光照樣」……一字一句,都在守護弱小,抵抗高牆。「政治從來都在身邊」,你們或許討厭這潭濁水,但我肯定,你們更加討厭的,是那道貌岸然的體制。反對建制的取態,除見於歌詞,還在你們的日常生活體現——阿偉會在facebook高呼「特首下台吧」;泥鯭每星期為潮流雜誌畫下,一幅又一幅諷刺時弊的漫畫;6號在添馬公園竭力呼籲群眾睜開眼,反國教。一舉一動,呼應歌詞,知行合一。在高牆與雞蛋之間,你們一直站在蛋的一邊。這一點毋庸置疑。
為公義上街的蛋
我記得,你們在紅館舞台說過,RubberBand最希望做的,是為港人帶來快樂。身為雞蛋,港人這幾年心情確實不快。因為不快,因為怨懟,好些人嘗試睜開雙眼,從沉睡中蘇醒,既有了身為雞蛋的自覺,也發現眼前那幅堅硬冰冷、無法踰越的高牆。高牆背後,有致力摧毁法治、勒緊自由、踐踏公義的高官,又有夷平豬籠墟,趕絕鐳射舖的地產霸權,表面相助,暗裏勾結。這些年來,高牆步步相逼,空間日漸萎縮。要爭取改變,我們唯有走上街頭,將脆弱不堪的身軀集結一起,如水流動,期望抵抗體制,衝擊高牆。
高牆的反擊,就是製造「巨蛋」。別誤會,這個聲稱與政府無關,卻竟可找來八大地產商聯手贊助興建的「巨蛋」,絕非實體,它只是一個幌子、一抹虛影,為的是營造虛假民意,轉移視線,打散蛋群——當這邊廂的雞蛋聚集維園,抵着陽光,爭取改變,那邊廂「巨蛋」矗立,又引來雞蛋圍觀,一同冒汗,欣賞演出。事後高牆便可下定論:其實走在軒尼詩道的蛋,不過是這城裏的少數!你看,海的另一邊更有蛋在狂歡!結果,為公義上街的蛋,被困在高牆與巨蛋中間,進退維園,左右為難。
當然,左右為難的,還有你們。海報面世以後,許多樂迷期望你們帶頭辭演,為蛋出一口氣。有人甚至聲言發起捐款,籌集違約款項。結果周五晚上,你們在facebook公開向支持者道歉,卻揚言「哪裏有舞台,哪裏都可以發聲」,堅持繼續參演,誓要在高牆上表達對「公義、公平和自由的訴求」。辭演,定能換來掌聲;留下,更有可能被繼續謾罵。於是消息公布後,有反對者說,RubberBand沒勇氣辭演,是「食兩家茶禮」,唯利是圖。這說法,我討厭——與其賭氣辭演,走入人群接受歡呼,倒不如勇敢留下,深入敵陣迎接噓聲,令更多人有機會覺醒。
把應該唱的唱出來
去年你們的紅館演出,全場氣氛最熱烈的一瞬,莫過於萬人合唱《睜開眼》。與同路人一同疾呼「在這刻睜開眼」,無疑教人激動,然而我更想說的是,在城市角落,在你我身邊,有更多的人仍然選擇沉睡,又或裝睡。你們「出事」後那早上,維穩騷的一萬八千張門票在三小時內售罊,網上炒風熾熱,特價九十九元的門票被抬高至數百元一張。為這場騷四出奔波,吶喊呼叫的一萬八千人,其實跟維園內的,一樣是雞蛋,只是他們不自知,又或不願知。在高牆進逼的年頭,依然有許多人覺得社會並無不妥,又或自己也改變不了什麼。他們認為,與其流汗白幹,不如蒙住兩眼,沉醉聲色,及時行樂。你知道的,令睡醒的人沮喪絕望的,從來都不是那看似牢固難倒的高牆,而是那明明受害卻不願睜開雙眼的雞蛋。
你們曉得村上春樹是在什麼場合講「牆與蛋」這個比喻嗎?二○○九年,他獲得「耶路撒冷文學獎」,而以色列正猛烈轟炸加沙。當年日本輿論極力勸阻他不要前去領獎,有人甚至警告,如果他出席,就會抵制他的書。此情此景,你們感覺熟悉吧?結果,村上堅持出席,並發表了家傳戶曉的〈牆與蛋〉,狠狠地摑了以國元首一把掌。至於那篇演辭,亦成為各地雞蛋與高牆對抗的推動力。我明白,村上的例子可能絕無僅有。你們站上「維穩巨星騷」舞台,可能會被人警告恫嚇,等看韓星的觀眾也可能對你們的熱心視若無睹。但那又如何?在這個陰霾籠罩的年代,又有誰保證高牆一定會傾倒,雞蛋一定會勝利?從來不。我們站出來,由維園走到中環,從來不因為這行動會換來實質的什麼;我們年復年,偏執走下去的源動力,從來都只是自己的良心,和信念。
「在大是大非的世代,有時我們需要的,應該就是一股勇氣,把應該唱的唱出來。」6號上月寫給家駒的公開信中,有這麼的一番話。七月一日,就請遵守諾言,用你們的結他和嘴巴,站在那曾經(在《天與地》)教人感動流涕的啟德平台,以言語為矛,用歌聲作箭,迎抗高牆,叫萬八隻裝睡的雞蛋蘇醒。我不懂得你們會遇上什麼險阻,只知道在你們背後,有萬千雙眼睛的支持。
這邊高牆,那邊巨蛋,我們這群雞蛋夾在中間,已無餘地再退一步。
It's all right. We're together.
從來不會丟低一個。
——RubberBand《夥伙》
阿果
刊於2013-06-23明報星期日生活封面
![]()
![]()
![]()
![]()
![]()
![]()
![]()
![]()
![]()
![]()